《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视野下的科技文化的伸张与确立,通过“大国重器”的命名及其文化史的钩沉是这本书的重要意旨所在。突出一种诗性,一种文化内在性,是其写作的根底。而科技本身的发展和在当代中国舆论场中的“新闻性”已然成为其写作的重要背景,而发现“诗意”也自然就拥有了为民族文化做注释的现实性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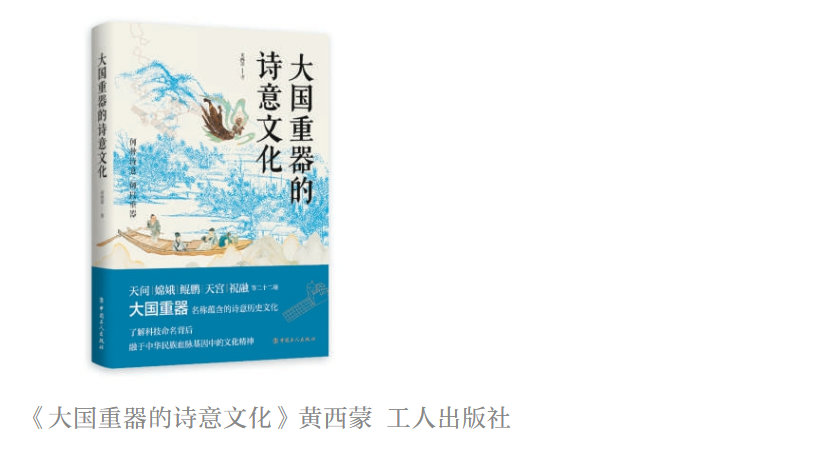
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人的本质,没有技术就没有人,人的进化其实是一种动物性退化和技术能力增强的历史过程。”如其所述,在技术与科学不断实现超越之时,人类正在因为自身的伟大创造和实践性力量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后人类”的现实状态。因为工具理性的充分张扬,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技术迭代的发生,使得人们更加确证技术作为“身体外在化的延伸”的重要意义。诚然,技术分明已成为一种人类力量对象化的产物,科学技术业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巨型话语系统”。根据刘易斯·芒福德的“巨机器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面对这套话语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慌乱。技术正在形成对人性的强力压迫和控制,这套“话语系统”是一种程式性的,并且因为这种程式性而编码出了一套人们难以逾越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可更改的技术体制、管理体制和文化体制。
相比于斯蒂格勒面对技术的中性主义,芒福德毋庸置疑向人类发出提醒,我们需要警惕技术至上的绝对主义。但相比之下,笔者更为倾向于斯蒂格勒的“中性主义”观点。而面对“技术统治”的当下,斯蒂格勒则倡导一种更为开放、更新、包容、适应的“技术文化”。因此,我们或许更能重新发现一种技术主义背景下的“诗意文化”的多重要义。
诚如黄西蒙在《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所言,书中所谓的“诗意”应该是包含着双重性的。第一是这些“大国重器”本身的命名蕴含着中国丰富的诗文元素,而作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命名出发勾连出内在性的文化诉求;第二,其内部所蕴含的这些文化内涵则充分显影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价值,作者要在行文的论述中重新发现这些“魅力和价值”,不仅要让自己懂得,更为重要的是让读者通过文本的阅读确立一种文化自信。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此明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和诗意写作的文体支撑”让斯蒂格勒所呼唤的一种全新的“技术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进程中拥有了一种“实存”的可能性。
《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是朝向科学技术的“巨型话语系统”的背面而去的写作。众所周知,科学主义的昌明,“赛先生”成为人们的共识是经历过长久的历史发展的。甚至可以说,五四时期的遗存问题依旧在当代作为一种常识性的丧失而屡被提醒和反复呼吁。因此,科普工作至今仍然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写作避开了作为一种“科普性写作”的短板,重在挖掘科技内在的民族文化精神,使得当代科技成为日常议程设置的重要话题。
比如,在《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第一章解读“天问”时,作者并未对探测器作为一种科学发明而深究其内在的技术原理,并未用一种科普式的写作对准探测器的发明史、探测器的技术演变史、探测器的现实意义等等。相反,作者从新华网、央视网等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入手,进而从“天问一号”探测器的名字展开其背后的历史性叙述。毋庸置疑,这种写作是一种避开“技术话语”的写作,写作者试图通过追求其名字背后的历史文化来达成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朝向科技这一“巨型话语系统”的背面展开一场人文主义的时代对话,这也是写作者唤醒读者内在的文化自觉性的有效策略。不做一般性的“科普”,而是去挖掘内在的民族心理程式、内在的文化秉性。整本书的写作策略基本都是沿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提供了一种当前人们面对技术主义强势话语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路径可能和表述策略,那就是用人文主义的方式去唤醒人们早已沉睡的心灵。通过一种避开“技术主义”的写作路径,在人们面前展开一种历史探寻的纵深感,让技术的现实性和工具理性在历史和文化面前褪去其功能主义和“非人性”的一面,还原技术本身内在所具有的人文性和艺术性。回到斯蒂格勒这里,他曾毫不避讳地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文化,以应对技术在大幅提升人类能力的同时对人类产生的反噬作用。”我想《大国重器的诗意文化》的出版是对这一论断的极好回应,也是让我们走出技术的迷雾丛林,避免方向迷失的良好方式。
(原标题:技术主义背景下的“诗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