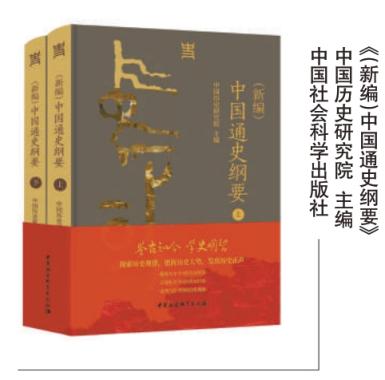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赓续不断的治史、修史传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薪火相传的文脉支点。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赓续不断的治史、修史传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薪火相传的文脉支点。
自司马迁著《史记》以来,以贯通古今、涵纳天下为旨要的通史撰述传统,即贯穿于两千余年历史演进之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历代史家肩负的治史使命,“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成为历代史家不懈追求的修史精神。“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正是透过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发展进程以及思想精华、价值理念得以呈现,得以流传,得以光大,厚植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历史底蕴,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一统、阔步向前的历史自觉。正是在“承敝通变”的特质导引下,众多“通史”经典之作,积淀着中华民族最醇厚的基因谱系,系著于历久弥新的精神塑造,表征于多元一体的基本图景,构成了中华文明生机盎然的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通史类著述,虽然多有史实硬伤,观点失之偏颇,但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上却有不小影响。编撰《(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就是要继承和弘扬我国治史、修史的优良传统,在一代代史学家理论建树和丰厚学术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按照新时代新要求,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以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展现中国史学新成就,呈现中国史学新思想,传递中国史学新表达,在国际史学思潮的激荡中,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正声,以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崭新风貌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注入强大能量。
中华文明是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称的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只有厘清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源头,才能真正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才能培育出文化自信的宏大气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雏形。根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形成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文明标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结构上出现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区域性“古国”政体或“早期国家”,形成各地区“相互作用圈”这一“最初的中国”形态。
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相继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古国”——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5300年前后,中国一些地区已经拥有更多“文明”社会的要素,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定论,拥有了充分的考古学实证。
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客观条件。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式与内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儒家学说为骨干的意识形态,为文明成长繁荣创造了条件。独特的史学传统造就了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文明传承意识。同域外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丰富发展的不竭动力。历经长期发展,中华文明培育出以道为统,以儒为基,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理念,以民本为政治思想基底,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核心,以通变革新为鲜明品格,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符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独特价值,凝聚多元区域和不同族群,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穷变通久、推陈出新中,展现出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具有从历史演进中探寻不变之常道的理性特质,“通古今之变”具有“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意义。文明史视野在当代中国史学的回归,映照着新时代最深切的关怀。当代中国的每一次创造,都是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自我更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仅带动了现代世界文明版图的大变化,而且向世界昭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昭示了更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现代化的形态,它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明土壤,以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为导引,发挥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在组织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效能;它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了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和而不同”“不齐而齐”的和平发展、和谐共享的世界秩序观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不是与传统断裂的新文明,也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而是从古老文明中走出来、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古今一贯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发展之路提供了全新启示和借鉴。
(本书编写组)
